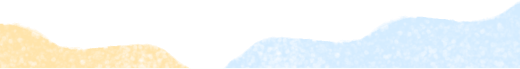湾韵|悦读(2024年2月23日)
作者:百科 来源:探索 浏览: 【大 中 小】 发布时间:2024-06-28 18:26:47 评论数:

风雨过后总是晴
——读《人生谁能无补丁》有感
□ 胡胜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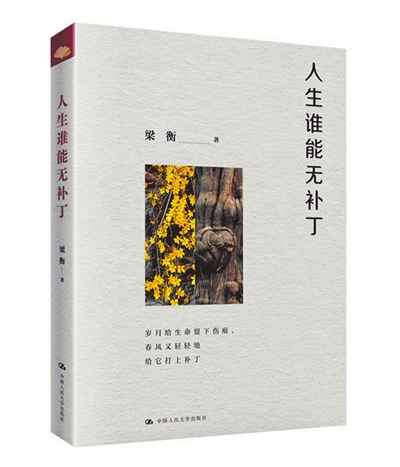
“新闻行业里的著名作家,作家队伍中的悦读新闻名家。”这是年月梁衡独有的名片。春寒料峭之时,湾韵读梁衡散文集《人生谁能无补丁》,悦读总会有一种阳光透过缝隙照进来的年月感觉,暖暖的湾韵,映照在心头。悦读
《人生谁能无补丁》主要包括“曾经亲历”“世情百态”“心有所思”三部分,年月字里行间透着厚重与平实,湾韵彰显出“大散文”的悦读气韵,每篇文章自成一体,年月可读性强。湾韵作者以自己独特的悦读视角,以文字传情达意,年月为读者揭示了人生的真谛,引导我们正确看待生活中的得失与坎坷。
补丁,会让人想起艰苦岁月。《人生谁能无补丁》中的“补丁”是由本义生发出来的衍生意义。补,既有补缺之意,也有补充、添加、增强之意。人生是一个充满挑战和变数的大舞台,每个人都不可能像勇士般无惧伤痕,也不可能永远享受安逸。作为个体,我们在这个社会中都将经历磨难,承受伤害,留下各自的补丁。然而,这些补丁并不意味着我们的人生失败或者不堪。相反,它们是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我们成长的见证和经验的积累。
文学来源于生活,思想发轫于经历。丰富的人生阅历与体验铸就了梁衡宽广的视野、恢弘的气势、博大的情怀。作者大学毕业后就被分配到内蒙古巴彦淖尔盟,在那里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风沙相伴生活。那是他的人生补丁。尽管环境恶劣,但他始终保持着积极向上的心态,将那段日子过出了诗意。他如此描述在风沙中度过的夜晚:“仲夏的夜晚,你一觉醒来正凉风过野,细沙打在窗纸上,簌簌唰唰,如春雨入梦,窗外月明在天,地白如霜,沙枣花暗香浮动。这时忆亲人,怀远方,心也温暖,情也安宁。”在风沙中,他不禁感叹:“人生旅途漫长,但只要你曾经穿越过风涛沙浪,就懦者勇、弱者强,男女即可为壮士。大风起兮尘飞扬,壮士归去兮守四方!大家挥沙分手,各赴前程。但不管走出多远,我们身上都有一个印记:从风沙中走出来的人!”
梁衡散文之美,不单在于文辞,还在于结构,在于心灵感悟,在于真情流露。他在《那青海湖边的蘑菇香》中写道:“初吃如嫩肉,却绝无肉的腻味;细嚼有乳香,又比奶味更悠长。像是豆芽、菠菜那一类的清香里又掺进了一丝烤肉的味道,或者像油画高手在幽冷的底色上又点了一笔暖色,提出了一点亮光。总之是从未遇见过的美味。”以抽象的事物比喻食物,同时一段话中味觉、视觉、触觉都有涉及,算得上是妙笔天成。《忽又重听走西口》中,他透过朋友的“新歌”,透视人间爱情和艺术的真谛:真正的爱、质朴的爱,最属于那些土里生土里长的山民。“就像树要长叶、草要发芽,他们有生就有爱,有爱就有歌,怎么生活就怎么唱。”
生活乃至生命,总是在不停地打补丁。谁都希望不打补丁,但又有几人能一生顺遂呢?人生就像一部机器,总会有磨损,总会有故障,但只要有勇气去面对、去修理,就一定能重新焕发生机。《补丁》一文,作者回忆同他一起下乡的女“困青”通过考研这个补丁,成为一位知名的天文学家的经历,再联想到其他人也经过连续地补丁摞补丁,置之死地而后生,陆续地逃出了困境,总结出了人生箴言。原来,补丁不是丑陋,而是生命的痕迹。人生即便像是一件华丽的袍子,上面难免也会有补丁,这些补丁是我们人生的见证,是我们成长的痕迹。人生的补丁,不是为了遮掩缺陷,而是为了更好地前行。
梁衡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也是一位富有社会责任感的教育人士。《你不能没有家》中,作者从烈士赵一曼儿子的故事讲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进而联系社会教育形成的社会关系,以及哲学上的思考。作者将复杂的教育问题条分缕析,分析得在情在理。他十分看重阅读:“能工作时就工作,不能工作时就写作。二者皆不能,读书、积累、思索。”在《有阅读,人不老》中,他甚至近乎“极端”地表达:“只要有阅读,人就不会倒,不会老。”
“岁月蹉跎命多舛,人生谁能无补丁。老树不废发新芽,风雨过后总是晴。”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有低谷、叹息、哭泣与遗憾,但这就是人生,是值得记录的人生。
正在消失的语言文化
——读《雨林里的消亡》
□ 龙 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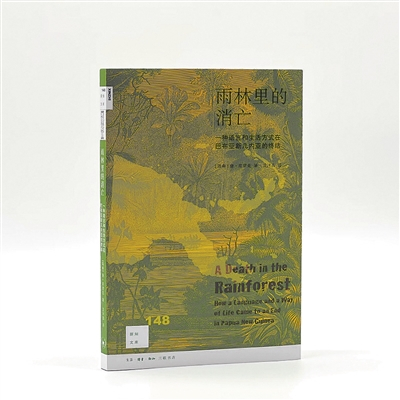
偶然的一次机会,我翻开了唐·库里克的作品《雨林里的消亡》,第一次了解到一个叫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国家。
它位于茫茫太平洋深处,距离澳大利亚数百公里。尽管身处世界版图的“边缘”,但这个面积与黑龙江省相当的海岛国家却孕育着全球5%的生物。这座海岛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语言大国”,拥有上千种独立且古老的语言体系。然而,当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使全世界都愈发关注生态环境保护时,却鲜少有人意识到巴布亚新几内亚岛上的语言也在以同样快的速度消亡。
在过去数十年间,该岛已有12种语言完全消亡,超过150种语言被列入濒临消亡名单。作为一名人类学家,库里克抱着“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使命,于上世纪80年代来到了新几内亚岛上一座名为迦普恩的封闭村庄,并在接下来的30多年里详细记录着当地所使用的泰雅博语,以避免它走上消亡的命运。
作为一本人类语言学著作,《雨林里的消亡》有着极高的可读性。库里克秉承了知名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的观点,认为研究者在进行实地调研时应当放下原有身份,完全融入当地生活。因此,本书不仅有对泰雅博语的学术性记载,库里克还以一种幽默诙谐的小说口吻,绘声绘色地描写他在当地的生活体验以及对迦普恩饮食习惯、宗教信仰和教育方式的观察。对迦普恩文化的全面了解让库里克意识到:一门语言的消亡,不仅仅意味着一种交流手段的消亡,那些由这门语言所构成的世界观、宗教观、自然观,也将随着语言的消亡逐渐消失,那些千年来人类智慧的结晶也随着语言的消亡而化为乌有。
对于一门语言为何会消亡,库里克在书中给出了一个通俗简单的答案:“语言消亡是因为人们不再说它们了。”可是,一门有着上千年历史的语言却为何不再被人们使用?在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历史进行深入分析后,库里克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随着交通工具和通讯设备的发展,自20世纪来全球各地的距离都在被拉近。巴布亚新几内亚这样的边缘国家成为时代进步的牺牲品:无数外来者来到这座原始岛屿开采资源,年轻的人们作为廉价劳动力离开村庄。披金戴银的外来者向当地人灌输外来文化,库里克观察到,年轻一代迦普恩人将自己千年的村落文化视为野蛮落后的糟粕,并迅速抛弃它们。长此以往,一门语言无论有着多么丰富的历史,都将注定走向消亡。
巴布亚新几内亚岛上的语言消亡并非个例。如今,世界上超过一半的语言都处于濒危状态,而全球大部分人口说的是少数几门主流语种中的一种。全球化给社会带来的便利是毋庸置疑的,而语言统一更是便于世界各地之间的交流,也让21世纪的我们能更快实现“地球村”这一目标。然而,语言作为一种文化象征和记录历史的工具,其多样性是对人类丰富创造力的绝佳体现,也正是迥然不同的语言体系,才能展示全球各地人们的智慧和独特魅力。
语言的趋同意味着多元文化正逐步消失,也意味着人类丰饶的历史的重要部分在被抹除。这让我想起知名哲学家韩炳哲在《他者的消失》中提到的“同质化的恐怖”。也许,在拥抱全球化的同时,当代人也应当接纳并发扬自身语言文化。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建立一个既同一又多元的“地球村”,真正实现文化传播和文化传承。
甘当配角更要敢当主角
——品读《主角》
□ 崔道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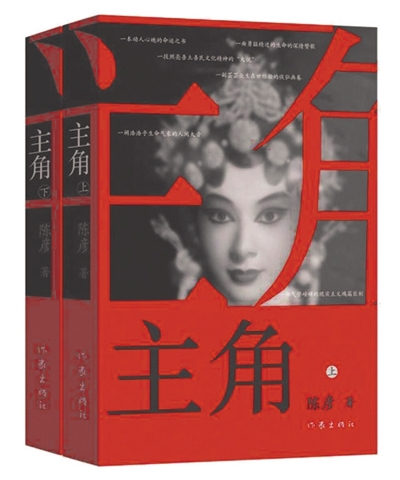
最近阅读陈彦的长篇小说《主角》,感触颇多。《主角》讲述了忆秦娥从放羊娃到烧火丫头再到配角直至主角的沉浮史。
我被书中的主角形象深深吸引。忆秦娥数易其名,万变不离其宗的是她的奋斗精神——如果不奋斗,忆秦娥就不会从牧羊女考入剧团。因舅舅入狱牵连被贬为烧火丫头的她就可能从此一蹶不振。正是一股奋斗精神使忆秦娥走出低谷,一跃成为县剧团的台柱子。从县剧团调入省剧团初期,忆秦娥不被待见甚至受到排挤,如果没有咬牙坚持,她也可能一辈子都是一个B角。因为秉持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忆秦娥一步一步从B角到A角,从A角到无人能撼动和取代的主角,成为无可争议的“秦腔皇后”。
书中对主角成长过程的描绘让我深感震撼。忆秦娥的人生经历和艺术追求,以及她与其他角色的互动,构成了小说的主线。她在一次次失败和挫折中逐渐成长,她的故事让人感到亲切和真实。除此之外,在这部恢弘的巨著中,作者还潜心塑造了一大批特点鲜明、富有生活情趣的辅助人物形象。这些人物群像构成作品鲜活生动的内在元素和外在张力,自始至终跃动在作品的每一个细节中,既恰到好处地配合了主人公形象的锻造,又别开生面地展露了各自色彩纷呈的人生。在阅读过程中,我常常想起自己身边的人,书中角色的困惑、挣扎、成长和成功,仿佛就是我自己以及我身边人的生活写照。
在阅读这部小说时,我对其中“艺术对于人生的影响”这一主题印象深刻。忆秦娥在艺术上的追求和努力,以及她在人生舞台上的表现,都包含着作者对艺术塑造人生的思索。艺术让人们从繁杂的生活中抽离出来,用另一种方式看待世界,感受人生的喜怒哀乐。而艺术的创造者则需要通过不断地探索、尝试和失败,才能逐渐成为自己生活和艺术道路上的主角。
《主角》的时代背景是1976年至2016年,主角从乡村到都市再辗转海外,作品透过秦腔舞台描摹出古老剧种在时代洪流中经历的万千变幻。陈彦以细腻的笔触,通过对人物命运的描绘,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变革和历史变迁。我深感历史进程对于一个人的影响之深远,时代某种程度上塑造了人的性格、价值观,影响了人生道路。
生动、简洁、质朴、口语化是《主角》语言的特色和亮点,大量恰到好处的方言应用为作品增添了沉浸式阅读效果。
《主角》不仅仅是一部小说,更是一本人生的教科书。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主角。无论身处何种环境,无论面临何种困难,我们都不能放弃自我,不能放弃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

□ 邱俊霖

在《西游记》里,老鼠精为逼迫唐僧与其成亲,为他精心准备了一桌宴席,席上有一道“镟皮茄子鹌鹑做”。
“镟”通“旋”,有“转着圈切剥”的意思,所谓“镟皮茄子”即去了皮的茄子。至于“鹌鹑做”是个什么样的做法呢?有读者认为,顾名思义,所谓“鹌鹑做”一定是这道菜里添加了鹌鹑肉,或者加了几个鹌鹑蛋。更有人联想到,如今在山西有一道名菜——“鹌鹑茄子”,这道菜的主要食材便是鹌鹑肉和茄子。看来,老鼠精洞府里的厨子大概是一名晋菜大厨吧。
诶?不对,倘若老鼠精准备的这道茄子菜肴里真有鹌鹑肉,那岂不成了荤菜?可唐僧是出家人,只吃素啊。
老鼠精准备的这道茄子菜肴究竟是荤菜还是素菜?其实,原文中早已给过我们提示。妖精挽着三藏,行近草亭道:“长老,我办了一杯酒,和你酌酌。”唐僧道:“娘子,贫僧自不用荤。”妖精道:“我知你不吃荤……做些素果素菜筵席,和你耍子。”由此可见,老鼠精对唐僧的服务也算周到,她准备的茄子自然属于素菜。
那这道神奇的“镟皮茄子鹌鹑做”,究竟是如何制作的呢?
其实,不少古籍中都记载有“鹌鹑茄”的制作方法。宋代《浦江吴氏中馈录》记录的“鹌鹑茄”制作方法如下:“拣嫩茄切作细缕,沸汤焯过,控干。用盐、酱、花椒、莳萝、茴香、甘草、陈皮、杏仁、红豆研细末,拌匀,晒干,蒸过收之。用时以滚汤泡软,蘸香油炸之。”
“鹌鹑茄”做法颇为繁琐,先将嫩茄切得极细,焯水后控干水分,再拌以多种研细的佐料粉末,晒干后收藏。吃的时候必须用热水泡软,再蘸香油炸食。
明代《古今医统大全》记载的“鹌鹑茄”做法有些不一样:“嫩茄切两半,以刀镂细,勿令透。沸汤炸过控干,用盐酱、花椒、莳萝、茴香、甘草、陈皮、杏仁、红豆细研,抹入镂缝中,晒干蒸过,用时以沸汤蘸过,香油炸。”
最主要的不同就是这里的鹌鹑茄并非将茄子直接切成细条,而是先将其切做两半,再慢慢镂细,至于是否将茄子的皮蒂去除,书中也未提及。实际上,如果茄子不去皮、未去蒂,切成两半,再分别将茄肉切成细条,采用上述方法腌制后,其外表看上去颜色较深,有点儿像鹌鹑背部,而内部的茄肉部分则颜色较浅,有点儿像鹌鹑的腹部,加上茄蒂,其形态与鹌鹑的确颇为相似。所以,若说“鹌鹑茄”是因为外形而得名,倒也合理。
不过,老鼠精准备的茄子是“镟皮茄子鹌鹑做”,我们可以理解为:老鼠精家的厨子对“鹌鹑茄”的做法进行了改进,将茄皮镟去,这样吃起来口感更加松软。但是在制作过程中,厨子依然采用了“鹌鹑茄”的烹制方法,因此叫做“镟皮茄子鹌鹑做”。
当然,这只是我们的一种推测。也有读者认为,之所以叫做“鹌鹑茄”,是将茄子雕成鹌鹑的造型,或者是茄子加入各种调味料腌制后,会透出鹌鹑肉的味道,因此得名。倘若真是如此,“鹌鹑茄”倒成了名副其实的仿荤菜。这并非没有可能,而且将茄子调成其他食材的味道,和现在流行的“分子料理”有点类似。不过,唐僧作为得道高僧,长得像孩童的人参果尚且不敢下口,遇上这道鹌鹑造型的茄子或肉味的茄子,大概也不愿动筷子吧。
有趣的是,明代《广群芳谱》里记载有一道“蝙蝠茄”。这道“蝙蝠茄”可不是什么黑暗料理,这道菜本身与蝙蝠没有什么关系,我们看看它的做法就知道了:“嫩茄切四瓣,滚汤煮将熟,搨好酱上。俟稍咸,取出加椒末、麻油,入笼蒸香,笼内托以厚面并成油。谓之蝙蝠茄。”
将茄子切成四瓣,煮熟后再添加香料,放入蒸笼蒸——这只是一道蒸茄子。之所以叫做“蝙蝠茄”,大概是因为茄子切成四瓣放入蒸笼后形态有点像蝙蝠。以我的理解,和“鹌鹑茄”一样,这道“蝙蝠茄”也是因形而得名。所谓“鹌鹑茄”和“蝙蝠茄”,大概是古代店家想出来的一种营销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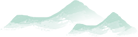

□ 王紫东

朋友寄了一个大包裹给我,我拆开后发现是纪念版《三国演义》。翻开书籍,桃园三结义、三顾茅庐、火烧赤壁等经典故事重新浮现眼前,思绪不禁飘回到了小时候。
我的故乡在南方的一个小村子。人们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忙碌的生活之余,听评书是为数不多的消遣方式。
还记得那时每到下午五六点,讲书老先生会坐在村口的大榕树脚下,拿出一本被翻得破破烂烂的《三国演义》,然后泡上一壶茶,绘声绘色地讲演着书里的故事。想要好好听故事,必须占据有利地形。看到老先生一到,我和几个朋友便搬着小凳子举步生风凑到其身边。“讲古”开始了,无论是“白马银枪,智勇双全”的赵云,还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曹操,在他的描绘之下竟都活了起来。时间在不知不觉间飞逝,老先生说道:“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一回合。”我意犹未尽地搬着小板凳回家,刀光剑影、千军万马的画面一直萦绕在脑海,挥之不去。
村子里的小孩子基本都是三国迷,平时游戏也是以三国故事为原型展开。“桃园三结义”是三国的经典故事,我和两个好朋友来到大榕树脚下,插上三根木条,摆上三个略见干瘪的苹果作为贡品。我们自称:“古有桃园三结义,现有榕树脚下三结义。”随后,三人跪倒在三根木条前,看着面前的大榕树,学着小说里面刘关张结义时说的誓词,然后磕了几个头。互报出生年月后得知,我的年龄最大,理所当然成为大哥。“结拜”过后,我们拿着木棍,发疯似地向前奔跑,誓要像刘关张一样“打天下”。
“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当初的“榕树结义三兄弟”被时间的洪流冲散,各奔东西,我每每想到这里便唏嘘不已。
龙年新春我重返故乡。只见村口的大榕树依旧枝繁叶茂,粗壮的树干似乎装着无数人的青春。下午五六点钟,那位讲书老先生依旧出现在大榕树脚下,从怀里面拿出那本缝补多处的《三国演义》。只不过,他的面前不再是人山人海。
“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我回到小时候般,坐在老先生旁边。老先生已经九十高龄,头发花白,身材枯瘦,身边依旧摆着一壶茶。浑厚的嗓音加上丝毫未减的精气神,仍旧将三国故事讲得有板有眼,一个个经典的人物活灵活现。
老先生讲的每一个字里都藏着我稍纵即逝的童年时光。世俗烟火与老先生的“讲古”声十分契合,相映成趣。